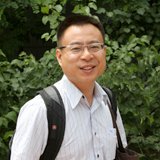電影再現文化地景—賽德克.巴萊Hold住台灣原味
從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到1990年代中期的台灣電影,回顧戰後台灣社會變遷乃至追索不同族群的生命故事,成為主要議題。當1990年代中期台灣電影下滑之際,也是另一道台灣風景浮現之時。歷經1990年代中期的社區總體營造,昔日幽暗的歷史得以撥雲見日。也是在1990年代中期,吳念真的《台灣念真情》建構了台灣島嶼上現實版的平民故事。這是一個重新發現台灣風景的起點。
再一次,魏德聖的電影引起狂潮。有趣的是,大眾從《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延伸出關於霧社事件史實的爭論 (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對於原住民文化當中祖靈 (Gaya) 的討論、莫那魯道以弱勢之姿挑戰文明自恃的日本一幕……,都在網路上被轉化為現實生活中自身或政治人物的寫照,從嚴肅到流行乃至惡搞,一切皆因《賽德克.巴萊》。
繪製新的台灣文化地景
電影研究學者陳儒修教授曾經在討論《練習曲》這部電影時,從後殖民的角度指出電影對台灣地景想像的變化:在過去,台北就是台灣的中心,但在《練習曲》中,這個台灣地理想像卻恰好反轉,電影中的主角從高雄出發,藉著單車旅行沿路記錄台灣各地的景象。如果從這個觀點延伸觀察這幾年的台灣電影,我們會發現台灣不同地方的特質不斷地浮現,如同博物館展示事物般再現台灣生活與文化,《賽德克.巴萊》及其他台灣電影也可從這個脈絡進行解讀。
然而,這些台灣電影影像中的地方性究竟從何而來?從1994年開展的社區總體營造,一方面借鏡日本的造町運動及「一鄉一特色」的實踐,另一方面,各地方的文化中心也透過老照片、口述歷史建構地方史。這是一個新的台灣地景想像的制度性基礎,也是地方多樣性浮現的開始。值得注意的是,伴隨社區總體營造與本土化風潮而來的,還有文化品味的翻轉:威權時期被壓抑的歌仔戲、布袋戲重新得到重視,近年來在城市行銷的脈絡下,夜市、美食也成為另一重台灣的重要地景。庶民生活品味已然成為重新發現台灣的產物。
此外,一個新的社會分類──四大族群 (福佬、客家、外省與原住民) 在1993年被提出,這個社會分類迄今仍被廣泛使用。不過,「族群」一詞在台灣有著不同層面的意涵:既有政黨政治的對抗,也有尋著社區總體營造走進庶民生活的文化探訪。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相對弱勢的政治社會處境、文化傳承的流失等,這個社會分類也可移轉為漢人與原住民的架構。
無論是社區總體營造或是四大族群分類,都試圖重新在歷史的基礎上找尋一個新的起點,一種新的台灣想像在這個起點上接續開展。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台灣電影導演們透過影像追尋台灣不同族群的歷史與身分認同,以及戰後台灣社會變遷下的成長故事;之後台灣電影便陷入一片沈寂,直到《海角七號》上映,才又重新引燃風潮。而這股風潮所展現的,不同於之前台灣電影的國族敘事或身分探尋,是透過影像再現前述台灣的庶民生活景象:小吃 (《雞排英雄》)、誠品 (《一頁台北》)、奠祭儀式 (《父後七日》) 等當今台灣生活的各種元素逐一顯現,台北不再是唯一。
《賽德克.巴萊》的歷史探索與展示
2011年,《賽德克.巴萊》結合了台灣新電影與後新電影導演們的企圖。不少台灣新電影導都有拍攝台灣 (人) 三部曲的企圖 (如侯孝賢、萬仁、王童等),不過在這當中,原住民是缺席的。
2002年,尚未成名的魏德聖在《小導演失業日記》書中立下心願,要拍出自己心目中的台灣人三部曲。《賽德克.巴萊》是魏德聖的第一部曲,而這一部曲填補了原住民的缺席。探索與展示是《賽德克.巴萊》的主軸,探索是指導演以一個漢人的身分切入原住民的歷史,展示則是導演透過影像再現原住民文化的核心元素。
就探索來說,魏德聖首先翻轉了昔日民族主義中心的莫那.魯道是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的這種說法 (1970年內政部的褒揚令如此表揚)。然而,一個漢人導演有什麼資格進入這個歷史事件當中?事實上,莫那.魯道是抗日英雄的說法在昔日的教育當中,已跨越漢人與原住民的界線,大家都曾接受過這樣的歷史敘事。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歷史敘事背後是日本的殖民統治。殖民政權所帶來的「殖民現代性」(既是殖民者,卻又帶來現代化) 問題,迄今仍困擾著台灣人,電影宣傳當中所說的「這是一個認同混淆的年代」,並不僅止於原住民。
其次,在某種程度上,魏德聖對霧社事件的探索也是對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回應。他在殖民者的「文明」與被殖民者的「野蠻」之間衝突的命題下,架構了歷史現場中幾種不同的角色:日本殖民政權的抵抗者 (如莫那.魯道)、合作者 (如鐵木.瓦力斯)、及在兩者之間的徬徨者 (如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在文明與野蠻背後,人們各有尊嚴、不同的律法及生活方式等。與其站在某種或大愛或大恨的立場來評斷這個時代,不如透過歷史現場中的不同角色進行討論。在這個意義上,霧社事件已然不是殖民者與原住民之間的問題,而是提供評價這段歷史的另一種可能性。
魏德聖的歷史企圖有著台灣新電影的味道,而《賽德克.巴萊》在很多片段中所展現的,與近年來台灣電影展示台灣的風格極為貼近。整部電影相當細緻地帶出原住民文化,全程的原住民語言、紋面儀式、出草、部落生活、音樂、舞蹈,也有不少屬於原住民表述方式的對白。最令人驚艷的,莫過於展示高山雄偉、地勢險峻的大場面,如果就台灣電影史來看,這恐怕是1970年代軍事政治宣傳電影的大場面之後,台灣電影唯一的鉅作。而且這些視覺效果也強化了文明與野蠻這組命題的對峙。
純就電影而言,《賽德克.巴萊》結構上的閃失,或許就在於歷史探索與原住民文化展示之間的平衡問題:某些段落如同劇情片地進行敘事,某些段落卻又如同紀錄片一般地展示,節奏的拿捏不無商榷之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賽德克.巴萊》在台灣所引燃的風潮,從嚴肅的原住民文化探索(如霧社事件的歷史真相) 到輕鬆的網友Kuso,乃至電影相關地點的旅行熱潮,電影文本只是其中一個核心原因。而電影文本如何外延與當下台灣社會連接,則又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編輯/龍傑娣
繪製新的台灣文化地景
電影研究學者陳儒修教授曾經在討論《練習曲》這部電影時,從後殖民的角度指出電影對台灣地景想像的變化:在過去,台北就是台灣的中心,但在《練習曲》中,這個台灣地理想像卻恰好反轉,電影中的主角從高雄出發,藉著單車旅行沿路記錄台灣各地的景象。如果從這個觀點延伸觀察這幾年的台灣電影,我們會發現台灣不同地方的特質不斷地浮現,如同博物館展示事物般再現台灣生活與文化,《賽德克.巴萊》及其他台灣電影也可從這個脈絡進行解讀。
然而,這些台灣電影影像中的地方性究竟從何而來?從1994年開展的社區總體營造,一方面借鏡日本的造町運動及「一鄉一特色」的實踐,另一方面,各地方的文化中心也透過老照片、口述歷史建構地方史。這是一個新的台灣地景想像的制度性基礎,也是地方多樣性浮現的開始。值得注意的是,伴隨社區總體營造與本土化風潮而來的,還有文化品味的翻轉:威權時期被壓抑的歌仔戲、布袋戲重新得到重視,近年來在城市行銷的脈絡下,夜市、美食也成為另一重台灣的重要地景。庶民生活品味已然成為重新發現台灣的產物。
此外,一個新的社會分類──四大族群 (福佬、客家、外省與原住民) 在1993年被提出,這個社會分類迄今仍被廣泛使用。不過,「族群」一詞在台灣有著不同層面的意涵:既有政黨政治的對抗,也有尋著社區總體營造走進庶民生活的文化探訪。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相對弱勢的政治社會處境、文化傳承的流失等,這個社會分類也可移轉為漢人與原住民的架構。
無論是社區總體營造或是四大族群分類,都試圖重新在歷史的基礎上找尋一個新的起點,一種新的台灣想像在這個起點上接續開展。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台灣電影導演們透過影像追尋台灣不同族群的歷史與身分認同,以及戰後台灣社會變遷下的成長故事;之後台灣電影便陷入一片沈寂,直到《海角七號》上映,才又重新引燃風潮。而這股風潮所展現的,不同於之前台灣電影的國族敘事或身分探尋,是透過影像再現前述台灣的庶民生活景象:小吃 (《雞排英雄》)、誠品 (《一頁台北》)、奠祭儀式 (《父後七日》) 等當今台灣生活的各種元素逐一顯現,台北不再是唯一。
《賽德克.巴萊》的歷史探索與展示
2011年,《賽德克.巴萊》結合了台灣新電影與後新電影導演們的企圖。不少台灣新電影導都有拍攝台灣 (人) 三部曲的企圖 (如侯孝賢、萬仁、王童等),不過在這當中,原住民是缺席的。
2002年,尚未成名的魏德聖在《小導演失業日記》書中立下心願,要拍出自己心目中的台灣人三部曲。《賽德克.巴萊》是魏德聖的第一部曲,而這一部曲填補了原住民的缺席。探索與展示是《賽德克.巴萊》的主軸,探索是指導演以一個漢人的身分切入原住民的歷史,展示則是導演透過影像再現原住民文化的核心元素。
就探索來說,魏德聖首先翻轉了昔日民族主義中心的莫那.魯道是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的這種說法 (1970年內政部的褒揚令如此表揚)。然而,一個漢人導演有什麼資格進入這個歷史事件當中?事實上,莫那.魯道是抗日英雄的說法在昔日的教育當中,已跨越漢人與原住民的界線,大家都曾接受過這樣的歷史敘事。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歷史敘事背後是日本的殖民統治。殖民政權所帶來的「殖民現代性」(既是殖民者,卻又帶來現代化) 問題,迄今仍困擾著台灣人,電影宣傳當中所說的「這是一個認同混淆的年代」,並不僅止於原住民。
其次,在某種程度上,魏德聖對霧社事件的探索也是對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回應。他在殖民者的「文明」與被殖民者的「野蠻」之間衝突的命題下,架構了歷史現場中幾種不同的角色:日本殖民政權的抵抗者 (如莫那.魯道)、合作者 (如鐵木.瓦力斯)、及在兩者之間的徬徨者 (如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在文明與野蠻背後,人們各有尊嚴、不同的律法及生活方式等。與其站在某種或大愛或大恨的立場來評斷這個時代,不如透過歷史現場中的不同角色進行討論。在這個意義上,霧社事件已然不是殖民者與原住民之間的問題,而是提供評價這段歷史的另一種可能性。
魏德聖的歷史企圖有著台灣新電影的味道,而《賽德克.巴萊》在很多片段中所展現的,與近年來台灣電影展示台灣的風格極為貼近。整部電影相當細緻地帶出原住民文化,全程的原住民語言、紋面儀式、出草、部落生活、音樂、舞蹈,也有不少屬於原住民表述方式的對白。最令人驚艷的,莫過於展示高山雄偉、地勢險峻的大場面,如果就台灣電影史來看,這恐怕是1970年代軍事政治宣傳電影的大場面之後,台灣電影唯一的鉅作。而且這些視覺效果也強化了文明與野蠻這組命題的對峙。
純就電影而言,《賽德克.巴萊》結構上的閃失,或許就在於歷史探索與原住民文化展示之間的平衡問題:某些段落如同劇情片地進行敘事,某些段落卻又如同紀錄片一般地展示,節奏的拿捏不無商榷之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賽德克.巴萊》在台灣所引燃的風潮,從嚴肅的原住民文化探索(如霧社事件的歷史真相) 到輕鬆的網友Kuso,乃至電影相關地點的旅行熱潮,電影文本只是其中一個核心原因。而電影文本如何外延與當下台灣社會連接,則又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編輯/龍傑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