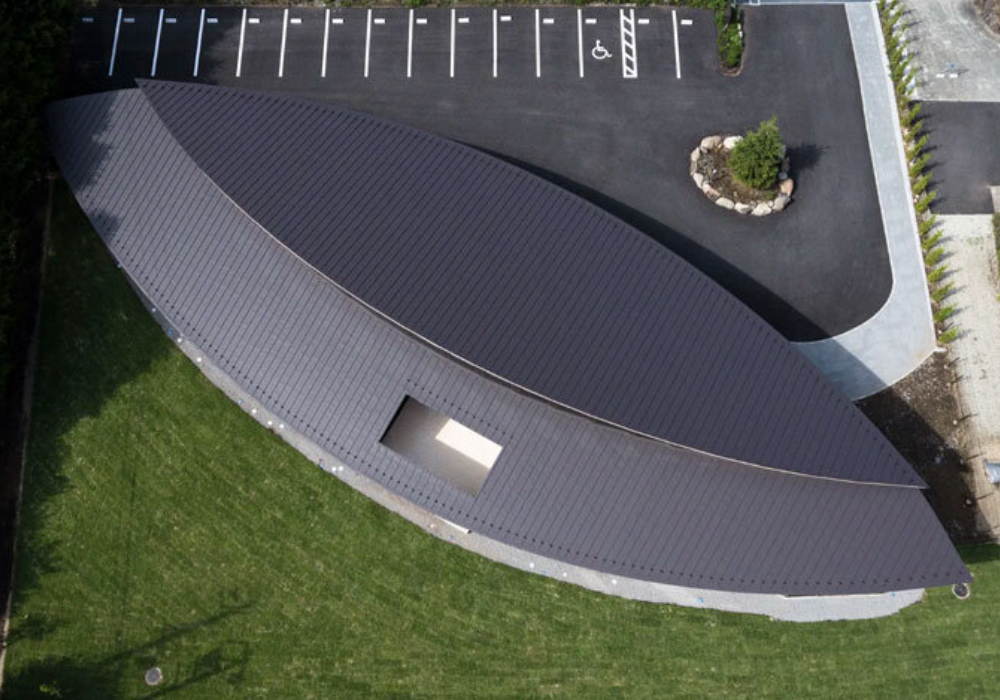好設計,點亮百萬人家
工業革命的十九世紀,世人普遍對「設計」一知半解。二十世紀初,工業設計師Raymond Loewy說:「當商品在相同的價格和功能下競爭時,消費者會選擇比較好看的那一個。」當時設計成為裝飾、點綴的代名詞。二十世紀末,IDEO提出了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一詞,正式將設計定義為一種體驗與思考的模式。逐漸地,設計開始滲透到人類生活中的每一個環節,變成一種強而有力的工具,倘若這工具能夠解決更多人所面臨的問題,世界將因此而美好。
2010年,當全球正為了垃圾污染、環境保護等問題傷腦筋的時候,一群MIT的學生透過 MyShelter 基金會以及各界贊助者的協助下,發明了「太陽瓶燈泡(solar bottle bulb)」。目前這項設計被廣泛運用於菲律賓境內,並期待 2012 結束前能提供100 萬個家庭所使用。太陽瓶燈泡適用於白晝中仍一片漆黑的空間,運用水的折射與漫射的原理將光引入室內,不需外接任何電力便能提供55瓦左右的光亮,並可持續使用五年之久,這些特性對菲國境內許多貧困家庭帶來極大效用。它的製作方式相當簡易,官方網站中甚至提供 DIY 步驟下載:在瓶內裝入清水混合漂白水 ﹝以防止發霉﹞,將屋頂開洞讓瓶子的下半身埋入室內空間,再將接合處修補、密合,便大功告成。
同樣由學生團體發起的還有 Design that Matters (DtM)。2001年,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開啟 DtM 概念,致力於運用創意和設計解決開發中國家的種種議題:飲水、弱勢族群、衛生保健、基礎教育與生活必需品等。DtM 招募數百名來自學界與業界的志願者共同組織智囊團,提供有需要的地區各種關鍵的解決方案。組織內的創新設計多以產品為主,例如低成本的眼鏡計畫、多項專利的醫療設備、微型膠片資料庫……。當時,DtM也以 2012 年為目標,希望屆時能累積一百萬個受惠者。
在這兩個例子中,可以清楚看見兩件事。第一、公益組織開始擺脫了原本口號式、抗爭式的層次,以設計作為手段和工具去實踐與改變。創造力往往是設計的核心能力:自古以來,人類靠著創造力演化,從輪子到引擎的種種發明,都是為了使生活更好過。同樣地,以設計中的創造力驅動公益活動的執行,未嘗不是人類提升生活方式和環境的本能。第二、在這裡,「關懷」似乎可以成為「為何設計 (Why to design)」的解答。關懷 (Care) 在英文中除了關心之外,還有憂慮與看護的意思;人們憂慮那些所需要憂慮之人事,除了將其放在心上,還必須更進一步的去看護、提供解決之道。當訴求的層次提昇,設計自然變得有價值,而當價值有了,在發想的過程中,想法往往也比較容易浮現,更重要的是創意也會變得比較務實。
台灣學生的思維總是反映出我們的語言架構與教育方式:以往,台灣產業以代工起家,代工的思維影響著我們社會與教育,如同《讓創意自由》一書的作者 Ken Robinson 的想法,目前的教育體制就像一座工廠,學生一入學就被貼上「一年級」的標籤,只能如同生產線一樣一級往一級爬升。等到爬升至最高級得已畢業時,你的畢業證書便清楚地印著你的入學與畢業年份,活脫脫的就像是食品檢驗合格證書中的製造日期及出廠日期。而當前的無薪假風波也許也和「工廠式教育」有關,當年電子業蓬勃發展時,許多莘莘學子受社會與家庭影響,紛紛投考電子相關科系,學校為了需求也廣開相關科系與研究所,導致「產量過剩」造成供過於求。然而,學校教育不應以創造經濟價值為目標,換言之,不該依據社會的需求而培養學生專才。台灣教育中長期忽視個體發展和獨特性,把教育視為進入社會企業的人才養成班,出廠就立刻進入下一個工廠化的職場。相反地,當我們願意花多點時間關懷個體,等個體成熟的時候,也會得到更多的回饋。
前不久,某台灣知名大學曾舉辦了一個與科技藝術相關的展覽會,不少達官顯要現身活動現場,可以見得該活動所受得重視,而會中官員也強調台灣科技在國際中數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發展科技藝術理當刻不容緩。再早之前,MIT多媒體實驗室所發起的One Laptop Per Child,OLPC計畫,當中 100 美元筆記型電腦便是由台灣廣達代工生產。這些都代表著台灣同樣有能力從島內發起自己的關懷計畫,串連學界與業界,運用科技的力量和設計力去思考更多島內的社會問題,籌劃屬於國人的「M.I.T」公益計畫。
編輯/林宛縈
編輯/林宛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