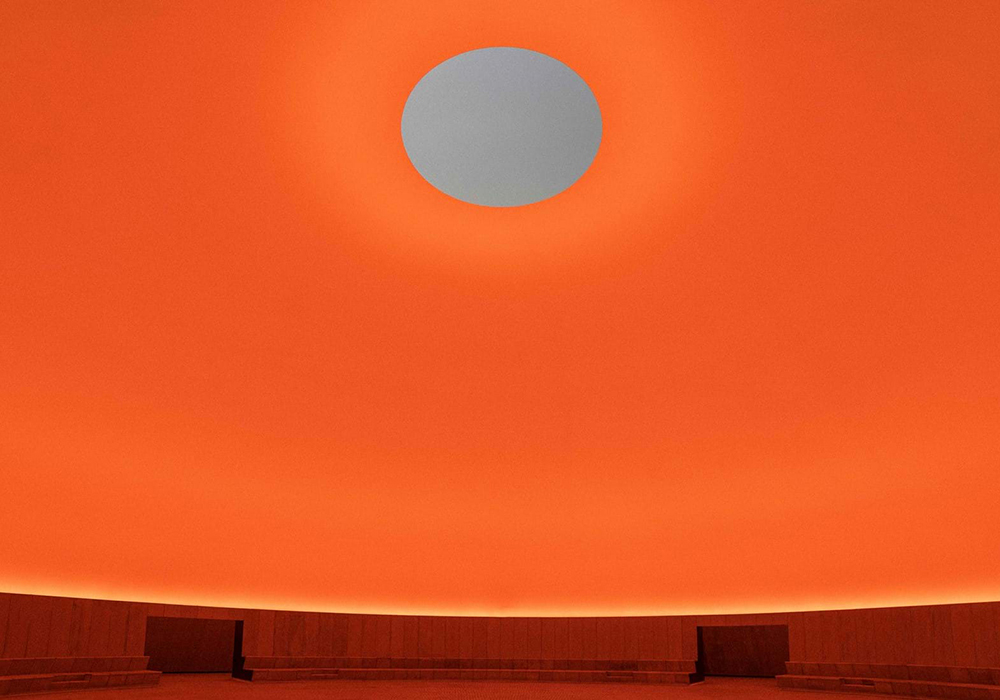我們對話並且抵抗─「生活作為形式」所帶來的自我覺察
本展探索20多年來,強調行動、實踐、對話與社群參與,模糊藝術形式與日常生活的文化行動與作品,以影音、文件的方式呈現,共分為「國際篇」與「在地篇」,前者展出至8月中,後者接續展至9月底,從全球回望台灣,以藝術介入社會,覺察、反省、矯正當前的傾斜現實。
應該如何統稱「生活作為形式」(Living as Form)所展出的文件(document),乃至於那些已然無法再現的藝術創作計畫?在目前展出的「 Part I 國際篇」中《屋頂上的熱血》(The Roof is on Fire)的創作者蘇珊.雷西(Suzanne Lacy)將這類做法稱為「新類型公共藝術」(New Genre Public Art)。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則是在《古堡裡的對話》這本書中使用「對話式藝術」(conversational art)來描述來描述這些以溝通、交流為主的藝術作品。我們不難從這些思想交會中看到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影子,他認為藝術創作可以視為一種溝通的場域。



在這個呈現差異的意義、詮釋與觀點的場域之中,作者的角色很明顯的被弱化了,我們不再需要去詢問創作者為何如此創作,因為作為文件的閱讀者或藝術創作當下的參與者,我們都不需要尋求創作者的存在經驗,從批判浪漫主義的觀點來看,作品不過是創作者存在經驗下的附屬品,用來憑證某種獨一無二的私人生活經驗,藝術是創作者本身自我覺察的陳述。
然而,我們持續幻想殺死「作者」多久了呢?這個幻想甚至已從模模糊糊的口號或宣示,發展成著名的思想學說。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走近亞陶〉(Approaching Artaud)一文便提及:「打從這個運動開始,其動力就是啓示錄式的——」,這段描述就像是意味著「殺死作者」的目標是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未來。但雷西口中的「新類型」似乎跡近完美的將「創作者的自我覺察」轉變成「社群的自我覺察」。創作者被消除掉,而社群中的角色慢慢地轉而清晰。
劇場結構的無限魅力是質疑意識形態 我們不如直接從《屋頂上的熱血》(左圖)談起。1994年某日黃昏時分,220位高中生在加州奧克蘭(Oakland)市中心的一個停車場上進行對話。他們坐在停車場的車子內,展開一系列的即興交談,討論加州有色族裔年輕人所面對的問題:包含媒體的刻板印象、具種族偏見的描述、公立學校資金不足等等,上千位奧克蘭居民,以及地方和全國性的媒體代表都被邀請去「旁聽」對話。顯然在形式上,這是劇場的結構。劇場的無限魅力來自於身處其中的角色有機會鬆動自己的政治性身分,這種鬆動使原本的發言權力者噤聲,轉而聆聽,表面上看來,是位於奧克蘭市中心停車場中車內的高中生在對話,事實上,對話發生在每個聆聽者的大腦中,他們正在與自己原始的政治身分抗爭。
我們不如直接從《屋頂上的熱血》(左圖)談起。1994年某日黃昏時分,220位高中生在加州奧克蘭(Oakland)市中心的一個停車場上進行對話。他們坐在停車場的車子內,展開一系列的即興交談,討論加州有色族裔年輕人所面對的問題:包含媒體的刻板印象、具種族偏見的描述、公立學校資金不足等等,上千位奧克蘭居民,以及地方和全國性的媒體代表都被邀請去「旁聽」對話。顯然在形式上,這是劇場的結構。劇場的無限魅力來自於身處其中的角色有機會鬆動自己的政治性身分,這種鬆動使原本的發言權力者噤聲,轉而聆聽,表面上看來,是位於奧克蘭市中心停車場中車內的高中生在對話,事實上,對話發生在每個聆聽者的大腦中,他們正在與自己原始的政治身分抗爭。在「生活作為形式」中所展出的藝術計畫,絕大部份都希望透過一種交流與對話過程,去鼓勵參與者質疑固定的身分認同、以及刻板形象。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詮釋:作家消除的越乾淨,這種交流與對話過程越能達到鬆動意識形態的效果。在這裡,我們反對透過一個具有觀點的圖像或物件,來製造一種單一、即刻的驚嚇經驗,理所當然地,我們也反對奇觀的創造,奇觀只是樹立另一種意識形態。然而,在本展中,也有這一類奇觀式的計畫。

 例如,艾未未參與第12屆卡塞爾文件展的藝術計畫《童話:一千零一位中國遊客》(右圖)。在整個計畫中,我們無時無刻不看見艾未未的巨大身軀,1001這個數字只是為了滿足天方夜譚的隱喻,甚至連隱喻都不足,計畫中完全沒有一千零一夜那種複雜且多元的敘事結構,至於「童話」就更膚淺了,只是因為卡塞爾當地那對最著名兄弟檔:童話家格林兄弟罷了,艾未未將1001位中國遊客帶離中國,帶他們離開生活,舉辦盛大的旅遊團,最後在艾未未敘事結構下成為盛大卻淡薄的背景後結束,難怪卡塞爾的展場上只放置了象徵性的1001張古董椅,而艾未未這個創作者,怎麼樣也殺不死。
例如,艾未未參與第12屆卡塞爾文件展的藝術計畫《童話:一千零一位中國遊客》(右圖)。在整個計畫中,我們無時無刻不看見艾未未的巨大身軀,1001這個數字只是為了滿足天方夜譚的隱喻,甚至連隱喻都不足,計畫中完全沒有一千零一夜那種複雜且多元的敘事結構,至於「童話」就更膚淺了,只是因為卡塞爾當地那對最著名兄弟檔:童話家格林兄弟罷了,艾未未將1001位中國遊客帶離中國,帶他們離開生活,舉辦盛大的旅遊團,最後在艾未未敘事結構下成為盛大卻淡薄的背景後結束,難怪卡塞爾的展場上只放置了象徵性的1001張古董椅,而艾未未這個創作者,怎麼樣也殺不死。與艾未未形成對比的,是凱特里娜.色達( Katerina Šedá)的計畫《那兒什麼都沒有》(There Is Nothing There),計畫名稱同時也是捷克的地方俗語。對位於捷克斯洛伐克彭多威斯(Ponetovice, Czech Republic)小鎮的居民來說,生活就如同那句俗語的意涵:「所有重要的事情都發生在城市和其他遙遠的地方」,我們無法忽略這句話對極權主義所帶來的挑逗,即: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使我們覺得自由」,正因為我們缺乏那些表達自由的語彙,缺乏是我們誤認自由的感受。
 色達在當地進行一年的訪查,觀察居民的日常生活。她邀請計畫參與者重新審視自我經驗。展覽中的文件紀錄下了2003年某日週六,居民的生活起居同步依照小鎮公佈欄上的行程表走,他們一起開窗、打掃陽台,出門購物,與朋友喝酒,最後十點準時睡覺。這些作息模式幾乎是每個彭多威斯居民的假日作息,然而一旦透過「表演日常生活」之後,這種社群集體意識的察覺過程使得計畫參與者有種解放感,這或多或少與蘇聯解體前,歐洲人民曾經擁有共同體驗有關,但這種解放感是居民在有意識的察覺自己的日常生活後,重新取得主體權力的真正自由。
色達在當地進行一年的訪查,觀察居民的日常生活。她邀請計畫參與者重新審視自我經驗。展覽中的文件紀錄下了2003年某日週六,居民的生活起居同步依照小鎮公佈欄上的行程表走,他們一起開窗、打掃陽台,出門購物,與朋友喝酒,最後十點準時睡覺。這些作息模式幾乎是每個彭多威斯居民的假日作息,然而一旦透過「表演日常生活」之後,這種社群集體意識的察覺過程使得計畫參與者有種解放感,這或多或少與蘇聯解體前,歐洲人民曾經擁有共同體驗有關,但這種解放感是居民在有意識的察覺自己的日常生活後,重新取得主體權力的真正自由。觀看文件的我們正有意識地對抗意識形態
我們無法忽視「生活作為形式」中每份文件所帶來的力量,它們的力量並非來自於藝術家將其欲表達內容囤積在某個被稱為藝術品的物件上而產生的,而是這些文件做為第二手媒體所產生的距離感,使們這些訊息接收者能更冷澈地審視其中的內容。儘管如此,我們從未因距離這些藝術計畫過遠,而對其所欲驅動的意識覺察感到事不關己,相反地,正因為保持距離,我們更能藉此鬆動自己的政治角色,不至於被藝術品吞噬,觀看文件的我們就像《屋頂上的熱血》計畫中的旁聽者,將我們連結在一起的,不是藝術家的意識,而是一連串對於藝術與更廣大社會及政治世界關係具挑釁性的想法,換句話說,這是我們正有意識地對意識形態進行抗爭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