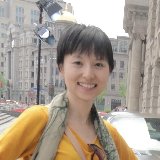王俊傑開啟數位迷宮花園
自2004年首次引進國際數位藝術展,王俊傑即帶領觀眾以「漫遊者」的身分,進入數位藝術的無限想像。然而,想像只是個開始。從去年底「2011超響」的聲音藝術、國美館的「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錄像藝術,到了今年「超旅程—2012未來媒體藝術節」,王俊傑以數位藝術的層層驚奇,開創一次次的奇幻之旅。這次,我們隨著王俊傑的步伐,一起踏上數位藝術的超時空旅程。這趟旅程交織著東西方的人文風景,除了炫麗奪目的聲與光,科技藝術也多了點溫度,有了對話,而成為了故事。
Q:從去年10月到今年1月,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您策劃參與了三個國際性數位藝術的展演陸續登場—「2011超響」、「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超旅程—2012未來媒體藝術節」,可否先請您介紹這三個展覽,並談談「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與國外策展人的合作方式與狀況,還有值得推薦的作品?
「超響」是從2008年開始籌辦,我們持續做了四年。去年的「2011超響」有點不一樣,我們想要轉型,我們以前比較偏向用數位或噪音來創作,但這只是聲音藝術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我們一直做相同的事情,會讓人家誤解聲音藝術是不是只有這種類型。所以,我們希望突破聲音藝術在台灣發展的形式,讓它可以更多元一點,把不同類型的聲音藝術引進來,做不同的嘗試。
國美館的「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又是另外一個類型。這次我們特別針對「錄像」單獨做一個展覽,這在台灣比較少見。這次規模很大,展出西方和台灣藝術家共53件作品。如果只放國際的錄像作品,意義好像不太夠,只能去觀摩。對西方而言,他們對於亞洲的錄像也不熟悉,而且還是從一個異國情調的角度來看。於是我和德國策展人討論,希望可以把東西對話的元素放進去。在展覽動線的安排上,將作品混在一起展出,對話性也許很曖昧,但也會很有趣。其實錄像已經變成一個很普遍的創作媒介,有必要對這個媒介做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討論,這個展覽在台灣有它的意義。
在此推薦這個展覽中的兩件作品:《歡慶(賽普勒斯街)》(Celebration (Cyprus Street), 2010),片中的英國倫敦的賽普勒斯街,有非常多不同族裔的移民住在那裡,導演在一個週末市集拍大家出來買東西或交談,然後大家聚集拍一張大合照,拍完之後就解散掉了。這在講種族和整個英國社會的關係,導演用35釐米拍,拍攝的方式介於觀念性的錄像藝術,又有點類似電影,手法很新穎,又有議題性。另一個推薦的作品是《共鳴》(Resonances, 2010),是關於一位女孩帶著耳機和麥克風,在大自然裡探索,片中聲音的呈現非常立體。
「超旅程」比較不一樣,是廣義的新媒體藝術展。我們有個企圖,就是想要談新媒體藝術的可能性。在台灣,通常不是很純粹藝術的表現,就是很應用性、很大眾化,或是帶遊戲性的。一般民眾不是覺得「啊,這個很藝術,看不懂」,不然就是覺得「啊,這個很好玩」。這樣很極端地去劃分,會讓民眾失去思考的機會。我覺得應該要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是從更純藝術的角度慢慢去介入這種應用性。我們希望這個展可以變成一個平台,去統合這個領域,一方面提供比較多的瞭解,一方面去思考這個媒體的可能性,還要兼顧冷僻的純粹藝術性,並具有高互動性的、遊戲性的特性。
Q:無論在視覺藝術或表演藝術,現今的「跨域合作」日漸成為一種趨勢。請問在這些展演的策劃與執行過程中,或是在藝術作品中,您觀察到藝術之間的跨域合作,如何成為可能?又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可否為我們舉一兩個例子。
「跨領域」本來就是一個趨勢,這也是「超旅程」展的特色和重點。有趣的是,很多作品是從跨領域的作品重新拿出來變成一個裝置,譬如《黃安妮計畫》的「人偶」裝置,就是在2011數位藝術節,和蕭賀文一起做表演。表演的時候,「偶」就是蕭賀文,是用蕭賀文的臉刻出來的,等於是一個鏡像,兩個會對話。但成為裝置時,因為已經沒有另外一個人和他對話,所以不需要去做這個寫實的對應,而重新做了一個新的偶。還有豪華朗機工的《游泳》,本來也是和周書毅合作,這次就把燈管獨立出來。
至於能擦出什麼「火花」,其實大都是無形中產生。譬如白南準的作品《萊特兄弟》,所使用的媒體和影像的裝置性,可以凸顯新媒體的特色,也可以展現「文化性」的部分。這是他比較晚期的作品,他回到韓國後,用了很多傳統亞洲元素和他所熟悉的西方元素結合在一起,所以他找了很多1960年代的古董電視,拼成兩個機器人,可是這兩個機器人看起來又像一架飛機。飛機象徵一種冒險,對於理想、想像的一種冒險。他把這個轉化成對於媒介的一種冒險,白南準的作品在整個展場的效果非常明顯。
Q:同時身為海外歸國的數位藝術家,您個人的學習背景與藝術家身分,對於策劃展覽是否帶來影響?
「策展」這件事情原本並不是我的生涯規劃(笑)。只是目前台灣一直沒有專業的策展訓練。我們在外國唸過書,可能對於西方如何用專業的角度去呈現展覽有些想像,所以有機會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身兼數職。這個情況不是很正常,卻是台灣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我的創作是比較觀念性、裝置性的,一兩年才能做一件作品,作品很龐大,所牽扯的面向很廣,所以我的角色比較像計畫的經理人或是策劃者,需要做很多精準的控制,把整個計畫統合好。當代藝術的創作和策展有點相似,就是扮演一個很好的統合角色。最重要的是組織力,這樣才能控制每一個環節。呈現出來的完成品,不管是一個作品或是展覽,都不能距離你的想像太遠,因為有可能不是你要的。
Q:在全球化、數位化的新媒體科技時代,東西方藝術與文化交流無國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您認為近年來台灣的數位藝術發展有哪些明顯的轉變?回歸到台灣本身的條件與環境,主要發展的瓶頸與可能性為何?
近幾年,台灣數位藝術的發展有進步,因為資訊交流的關係,所以可以很快知道外面發生的事情,而年輕的創作者也會有新的想法、新的技術,或是新的能力。但從各種面向來看,台灣面臨一個瓶頸,就是無法突破一種規模性的尺度,這是整體大環境的問題,例如教育制度、政府政策和所有層面能不能結合在一起。環境的變化必須跟得上創作的動能,如果跟不上,就只能維持在一定的狀態裡面,無法很快地躍進或進步。
如何發展出我們自己獨特的風格或語言?這是這個產業的人都要追求的。我們現在好像還是一個追隨者,追隨西方或先進國家的一個角色。能否突破外面的競爭,產生個人獨特的創意或方向,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重點是我們有沒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Q:對於國際性的數位藝術展覽或表演,您未來是否還有相關的計畫?透過這些未來的展演,您希望對於台灣的數位藝術發展,達到哪些理想與期望?
在策展的部分,目前沒有非常具體的計畫,但已經在思考做一個類似國美館錄像展的展覽,因為這個展是從西方的角度出發,並不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動態影像(moving image) 已成為新的文化主流,但目前我們好像沒有系統性地去處理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創作計畫,是一個比較大規模、跨領域的無人劇場表演,希望與更多的藝術家合作,找出新的創作語言。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突破現有的創作規模,產生更大的技術或是視野。
畢竟一個人一輩子的精力有限,做什麼事情其實不是很重要,重點是做的事情是不是有「開創性」,而且還可以有一種「累積性」。對於同輩、學生或年輕創作者,是否可能產生一些影響,去做一些整合,這個意義會比較大。
「超響」是從2008年開始籌辦,我們持續做了四年。去年的「2011超響」有點不一樣,我們想要轉型,我們以前比較偏向用數位或噪音來創作,但這只是聲音藝術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我們一直做相同的事情,會讓人家誤解聲音藝術是不是只有這種類型。所以,我們希望突破聲音藝術在台灣發展的形式,讓它可以更多元一點,把不同類型的聲音藝術引進來,做不同的嘗試。
國美館的「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又是另外一個類型。這次我們特別針對「錄像」單獨做一個展覽,這在台灣比較少見。這次規模很大,展出西方和台灣藝術家共53件作品。如果只放國際的錄像作品,意義好像不太夠,只能去觀摩。對西方而言,他們對於亞洲的錄像也不熟悉,而且還是從一個異國情調的角度來看。於是我和德國策展人討論,希望可以把東西對話的元素放進去。在展覽動線的安排上,將作品混在一起展出,對話性也許很曖昧,但也會很有趣。其實錄像已經變成一個很普遍的創作媒介,有必要對這個媒介做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討論,這個展覽在台灣有它的意義。
在此推薦這個展覽中的兩件作品:《歡慶(賽普勒斯街)》(Celebration (Cyprus Street), 2010),片中的英國倫敦的賽普勒斯街,有非常多不同族裔的移民住在那裡,導演在一個週末市集拍大家出來買東西或交談,然後大家聚集拍一張大合照,拍完之後就解散掉了。這在講種族和整個英國社會的關係,導演用35釐米拍,拍攝的方式介於觀念性的錄像藝術,又有點類似電影,手法很新穎,又有議題性。另一個推薦的作品是《共鳴》(Resonances, 2010),是關於一位女孩帶著耳機和麥克風,在大自然裡探索,片中聲音的呈現非常立體。
「超旅程」比較不一樣,是廣義的新媒體藝術展。我們有個企圖,就是想要談新媒體藝術的可能性。在台灣,通常不是很純粹藝術的表現,就是很應用性、很大眾化,或是帶遊戲性的。一般民眾不是覺得「啊,這個很藝術,看不懂」,不然就是覺得「啊,這個很好玩」。這樣很極端地去劃分,會讓民眾失去思考的機會。我覺得應該要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是從更純藝術的角度慢慢去介入這種應用性。我們希望這個展可以變成一個平台,去統合這個領域,一方面提供比較多的瞭解,一方面去思考這個媒體的可能性,還要兼顧冷僻的純粹藝術性,並具有高互動性的、遊戲性的特性。
Q:無論在視覺藝術或表演藝術,現今的「跨域合作」日漸成為一種趨勢。請問在這些展演的策劃與執行過程中,或是在藝術作品中,您觀察到藝術之間的跨域合作,如何成為可能?又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可否為我們舉一兩個例子。
「跨領域」本來就是一個趨勢,這也是「超旅程」展的特色和重點。有趣的是,很多作品是從跨領域的作品重新拿出來變成一個裝置,譬如《黃安妮計畫》的「人偶」裝置,就是在2011數位藝術節,和蕭賀文一起做表演。表演的時候,「偶」就是蕭賀文,是用蕭賀文的臉刻出來的,等於是一個鏡像,兩個會對話。但成為裝置時,因為已經沒有另外一個人和他對話,所以不需要去做這個寫實的對應,而重新做了一個新的偶。還有豪華朗機工的《游泳》,本來也是和周書毅合作,這次就把燈管獨立出來。
至於能擦出什麼「火花」,其實大都是無形中產生。譬如白南準的作品《萊特兄弟》,所使用的媒體和影像的裝置性,可以凸顯新媒體的特色,也可以展現「文化性」的部分。這是他比較晚期的作品,他回到韓國後,用了很多傳統亞洲元素和他所熟悉的西方元素結合在一起,所以他找了很多1960年代的古董電視,拼成兩個機器人,可是這兩個機器人看起來又像一架飛機。飛機象徵一種冒險,對於理想、想像的一種冒險。他把這個轉化成對於媒介的一種冒險,白南準的作品在整個展場的效果非常明顯。
Q:同時身為海外歸國的數位藝術家,您個人的學習背景與藝術家身分,對於策劃展覽是否帶來影響?
「策展」這件事情原本並不是我的生涯規劃(笑)。只是目前台灣一直沒有專業的策展訓練。我們在外國唸過書,可能對於西方如何用專業的角度去呈現展覽有些想像,所以有機會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身兼數職。這個情況不是很正常,卻是台灣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我的創作是比較觀念性、裝置性的,一兩年才能做一件作品,作品很龐大,所牽扯的面向很廣,所以我的角色比較像計畫的經理人或是策劃者,需要做很多精準的控制,把整個計畫統合好。當代藝術的創作和策展有點相似,就是扮演一個很好的統合角色。最重要的是組織力,這樣才能控制每一個環節。呈現出來的完成品,不管是一個作品或是展覽,都不能距離你的想像太遠,因為有可能不是你要的。
Q:在全球化、數位化的新媒體科技時代,東西方藝術與文化交流無國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您認為近年來台灣的數位藝術發展有哪些明顯的轉變?回歸到台灣本身的條件與環境,主要發展的瓶頸與可能性為何?
近幾年,台灣數位藝術的發展有進步,因為資訊交流的關係,所以可以很快知道外面發生的事情,而年輕的創作者也會有新的想法、新的技術,或是新的能力。但從各種面向來看,台灣面臨一個瓶頸,就是無法突破一種規模性的尺度,這是整體大環境的問題,例如教育制度、政府政策和所有層面能不能結合在一起。環境的變化必須跟得上創作的動能,如果跟不上,就只能維持在一定的狀態裡面,無法很快地躍進或進步。
如何發展出我們自己獨特的風格或語言?這是這個產業的人都要追求的。我們現在好像還是一個追隨者,追隨西方或先進國家的一個角色。能否突破外面的競爭,產生個人獨特的創意或方向,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重點是我們有沒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Q:對於國際性的數位藝術展覽或表演,您未來是否還有相關的計畫?透過這些未來的展演,您希望對於台灣的數位藝術發展,達到哪些理想與期望?
在策展的部分,目前沒有非常具體的計畫,但已經在思考做一個類似國美館錄像展的展覽,因為這個展是從西方的角度出發,並不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動態影像(moving image) 已成為新的文化主流,但目前我們好像沒有系統性地去處理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創作計畫,是一個比較大規模、跨領域的無人劇場表演,希望與更多的藝術家合作,找出新的創作語言。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突破現有的創作規模,產生更大的技術或是視野。
畢竟一個人一輩子的精力有限,做什麼事情其實不是很重要,重點是做的事情是不是有「開創性」,而且還可以有一種「累積性」。對於同輩、學生或年輕創作者,是否可能產生一些影響,去做一些整合,這個意義會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