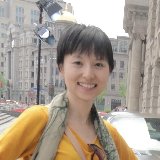「我」和「我們」的生命旅程《生之曼陀羅》——林秀偉專訪
睽違10年,未再一起共舞的林秀偉與吳興國,此次應MOT/ARTS的「Art For The Masses」計畫之邀,再度重新詮釋1988年的作品《生之曼陀羅》,火紅慾望、身體纏繞、衝突撕扯,舞作《生之曼陀羅》既神秘又富有強烈感官衝擊,訴說的是一個人的生命之旅。
而MOT/TIMES也藉此機會,專訪到林秀偉,除了聊聊這支舞作、參與Art For The Masses計畫的過程之外,出乎我們預期的,林秀偉更大方地為我們揭露了吳興國嚴肅外表下,居家、可愛、調皮的那一面,瞬間讓人覺得與兩位表演藝術家距離拉近許多呢。
而MOT/TIMES也藉此機會,專訪到林秀偉,除了聊聊這支舞作、參與Art For The Masses計畫的過程之外,出乎我們預期的,林秀偉更大方地為我們揭露了吳興國嚴肅外表下,居家、可愛、調皮的那一面,瞬間讓人覺得與兩位表演藝術家距離拉近許多呢。
MOT/ARTS 今年的「Art For The Masses」計畫,以「我‧我們」為展出主題,邀請到林秀偉、吳興國及向京、瞿廣慈兩對夫妻藝術家共同創作,以「我」和「我們」為討論切點,從「我」的主體意識,透過雕塑與手動舞蹈影像裝置的相互詮釋、辯證與對話,交換彼此的生命主題,共同討論關乎「我們」的生命共通性和普世價值。
而為了這次的展覽,林秀偉和吳興國則是選擇1988年的作品《生之曼陀羅》,做為和向京與瞿廣慈對話的起點。
或許,生命是一趟旅行,每個人習慣用自己的方式來完成,吳興國和林秀偉選擇的便是「身體」。無論是當代傳奇劇場的《慾望城國》、《李爾在此》、《等待果陀》,還是太古踏舞團的《生之曼陀羅》、《無盡胎藏》,他們不斷挑戰身體的可能性,為自己的生命旅程添加了更多姿態與表情。只是過去無數次的角色扮演,是從他人的視角反視生命旅程的面貌,在這次的《我‧我們》,兩人選擇回到真實的自己,用《生之曼陀羅》的愛恨嗔癡,訴說兩人共同經歷的生命旅程,一個「我」和「我們」的生命故事,映照著兩人的創作,還有生活。
那麼,究竟《生之曼陀羅》是一段什麼樣的「我」和「我們」的故事,就讓主角之一的林秀偉現身說法,為我們一一道來。
Q:可以先跟我們談談《生之曼陀羅》(1988年作品)這支舞作嗎?
A:一件作品不見得是作者個人的故事,有可能是作者周遭所發生的生命故事,而《生之曼陀羅》背後就有一個悲傷的故事。
 當代傳奇劇場在1986年成立,那時我們做了《慾望城國》,燈光設計是周凱,那時大家都年輕,就想一路往前衝,相信人定勝天。一開始《慾望城國》演出後得到很多肯定與掌聲,後來有個國際的經紀人到台北來,我們決定再加演一場,但因為很臨時,很多人都超時工作,可能是因為太疲憊,準備工作時周凱就從調燈架摔下來,過世了。這個衝擊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大,那一刻讓我覺得,原來生命不是你怎麼控制,就可以走到目的的。
當代傳奇劇場在1986年成立,那時我們做了《慾望城國》,燈光設計是周凱,那時大家都年輕,就想一路往前衝,相信人定勝天。一開始《慾望城國》演出後得到很多肯定與掌聲,後來有個國際的經紀人到台北來,我們決定再加演一場,但因為很臨時,很多人都超時工作,可能是因為太疲憊,準備工作時周凱就從調燈架摔下來,過世了。這個衝擊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大,那一刻讓我覺得,原來生命不是你怎麼控制,就可以走到目的的。
《生之曼陀羅》就是在講這樣一個人的生命旅行,從出生、產生愛、產生慾望、對立和衝突,到最後進入黑暗,但又努力尋找心裡僅存的火苗,重新燃燒熱情,迎接明天的太陽。而兩個來自不同時空的人,他們在某一個時空相遇,可能是擦肩而過,可能閃耀出火光,那個火光可能很巨大,可以照亮彼此的生命,《生之曼陀羅》就是在講這樣的故事。


Q:這次Art For The Masses的主題為「我‧我們」,請再細談這個主題和《生之曼陀羅》的關連性。
A:我們的創作,是「我」,也是「我們」一起完成的,而我在創作的時候,最常碰到第二個我就是吳興國。我們兩個都是彼此的第二個我,我們很像一個大肉球,只不過是被撕扯變成一半,像希臘悲劇一樣,分不清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不過有時候我更覺得他就像是我的小孩,他是不是我生出來的呢?
Q:所以兩個人之間可以不用言語溝通就彼此瞭解?
A:應該是說我猜他猜得準,他猜我猜不準,哈。
比方說當我看到他在偷笑,我就知道他背著我偷做了什麼壞事;你們看他的樣子,會覺得他很嚴肅,但其實他是很怕陌生人的,而且他非常調皮,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記得我女兒還小的時候,他們兩個會在餐廳裡面打來打去,我覺得好可怕,這麼老的人怎麼還在那邊跑來跑去。不過他也很容易生氣,我覺得他就像是幼稚園大班的小孩,而且是全班最難帶的那個,他可能會爬到樹上,又會躲在牆角不跟你講話,耍自閉。
Q:耍自閉的時候,是期待大家瞭解他嗎?
A:他不會,他根本不甩(笑)。
Q:彼此在生活或是創作上相互扮演的角色?
A:我覺得他是一塊石頭,而他覺得我像水,水可以移動石頭到原本不願意去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也覺得我像火,所以我就是水和火的綜合體。有時候,他也可以說是一棵樹,紮好根後,哪裡都不願意去,情願孤芳自賞,但是我會給他水,給他陽光,讓他再多開點花。
在工作上,我則是個工作狂,吳興國都叫我鐵娘子,但是因為有我,他才有安全感。聽說如果表演之前我還沒有出現,吳興國就會在那邊走來走去,只要我一出現,他就會安心下來。有趣的是,我女兒說我和吳興國不是愛人,是兄弟。
Q:這和我們的既定印象不太一樣。
A:對,其實我們就像太陽和月亮一樣,都有著陰陽兩面不停地在交換,無論是溫度或明暗度,所以在《生之曼陀羅》中有一些雙頭獸的造形,一個身體兩個腦袋,這就是我們相處的表現。





Q:這次Art For The Masses也邀請向京和瞿廣慈一同參與,可以跟我們分享對於他們作品的看法嗎?
A:我覺得向京的心思很細膩,她的作品好像一直保持在15、16歲少女的狀態,皮膚彈指可破,要被小心地保護著,放在一個永恆的花園裡面,不受污濁世界的沾染。我覺得女性很適合收藏她的作品,因為女人心中總保有對這世界嚮往的一處,而向京則是把那一刻留在她的作品裡。
瞿廣慈則是用作品來嘲笑這個世界的體制,諷刺人的權力就像打腫臉充胖子,雖然胸懷大志,長了翅膀,可卻是飛不起來。這隻鳥所佔領的樹,也是一顆假樹,像個謊言,就像莎士比亞說的,假樹怎麼會結出真的果子呢。所以他透過作品影射社會、政治的樣貌都是虛假的。



Q:「身體」是雙方創作的一個共通性,可否跟我們分享在這件作品中,雕塑和舞蹈表現身體形式的差異?
A:在向京的作品中,我看到某種優雅的姿態,脖子很長,身體很纖細,像精靈一樣。而看我們的作品,我覺得我是女巫,而向京是精靈,不過,精靈與女巫也是同一件事,輕靈是種力量,毀滅也是,這是二元的,是土地和天空的力量,可以互換。
Q:怎麼看待這次「跨領域」的合作方式?
A:其實跨領域對我們並不陌生,只是以前是由我們為本體,邀請別的藝術家,比方說葉錦添、張大春、徐克。這次比較是「對話性」的,很像是彼此相連,又有交錯,但是又分道揚鑣,只是有一個共同的核心精神,來講述「我」跟「我們」之間的故事,從肢體或是從美術上,有點對照的感覺。
Q:談談這次《生之曼陀羅》的呈現形態,從現場的舞蹈表演轉變成手動影像的表現,您怎麼看待作品呈現方式的改變?
A:我覺得這樣的處理方式很有趣,把我們縮得很小,縮在一個古老的鏡頭裡面,還蠻神秘的。因為《生之曼陀羅》其實是個慾望的世界,框在裡頭,好像是人生愛情的顯微鏡,挺有意思的。
而用手動操作的方式,讓觀者參與表演,觀看的當下就像是在表演觀者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這樣的展出方式,就像創造了一個機會說觀賞者的故事,《生之曼陀羅》就不只是我和吳興國的故事。



Q:這次重新演出《生之曼陀羅》,和之前的演出有什麼樣的改變?
A:其實我和吳興國已經快10年沒有一起跳舞了。這次我們一次排練都沒有,就這樣子去拍了,一次就成功了,我自己也感到很驚訝。吳興國說我除了重了一點以外,沒有什麼改變,不過既然他還抬得動我,所以我也沒那麼重嘛(笑)。
 1988年我們跳完《生之曼陀羅》後,我女兒就出生了,而這次展覽的記者會,也請我女兒跳一支舞(右圖),為展覽開場,所以若說這隻舞和過去有什麼不一樣?我想,應該是多了「傳承」這個意義。
1988年我們跳完《生之曼陀羅》後,我女兒就出生了,而這次展覽的記者會,也請我女兒跳一支舞(右圖),為展覽開場,所以若說這隻舞和過去有什麼不一樣?我想,應該是多了「傳承」這個意義。
Q:如果有來生,兩位還想再當夫妻嗎?
A:吳興國曾經對我說他來生想變成一棵樹,我聽到以後,就笑著回答他:「那我要變成樹上面的那隻猴子,你想要安靜,我就在你身上盪來盪去,讓你不得安寧。」
而為了這次的展覽,林秀偉和吳興國則是選擇1988年的作品《生之曼陀羅》,做為和向京與瞿廣慈對話的起點。

或許,生命是一趟旅行,每個人習慣用自己的方式來完成,吳興國和林秀偉選擇的便是「身體」。無論是當代傳奇劇場的《慾望城國》、《李爾在此》、《等待果陀》,還是太古踏舞團的《生之曼陀羅》、《無盡胎藏》,他們不斷挑戰身體的可能性,為自己的生命旅程添加了更多姿態與表情。只是過去無數次的角色扮演,是從他人的視角反視生命旅程的面貌,在這次的《我‧我們》,兩人選擇回到真實的自己,用《生之曼陀羅》的愛恨嗔癡,訴說兩人共同經歷的生命旅程,一個「我」和「我們」的生命故事,映照著兩人的創作,還有生活。
那麼,究竟《生之曼陀羅》是一段什麼樣的「我」和「我們」的故事,就讓主角之一的林秀偉現身說法,為我們一一道來。
Q:可以先跟我們談談《生之曼陀羅》(1988年作品)這支舞作嗎?
A:一件作品不見得是作者個人的故事,有可能是作者周遭所發生的生命故事,而《生之曼陀羅》背後就有一個悲傷的故事。
 當代傳奇劇場在1986年成立,那時我們做了《慾望城國》,燈光設計是周凱,那時大家都年輕,就想一路往前衝,相信人定勝天。一開始《慾望城國》演出後得到很多肯定與掌聲,後來有個國際的經紀人到台北來,我們決定再加演一場,但因為很臨時,很多人都超時工作,可能是因為太疲憊,準備工作時周凱就從調燈架摔下來,過世了。這個衝擊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大,那一刻讓我覺得,原來生命不是你怎麼控制,就可以走到目的的。
當代傳奇劇場在1986年成立,那時我們做了《慾望城國》,燈光設計是周凱,那時大家都年輕,就想一路往前衝,相信人定勝天。一開始《慾望城國》演出後得到很多肯定與掌聲,後來有個國際的經紀人到台北來,我們決定再加演一場,但因為很臨時,很多人都超時工作,可能是因為太疲憊,準備工作時周凱就從調燈架摔下來,過世了。這個衝擊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大,那一刻讓我覺得,原來生命不是你怎麼控制,就可以走到目的的。《生之曼陀羅》就是在講這樣一個人的生命旅行,從出生、產生愛、產生慾望、對立和衝突,到最後進入黑暗,但又努力尋找心裡僅存的火苗,重新燃燒熱情,迎接明天的太陽。而兩個來自不同時空的人,他們在某一個時空相遇,可能是擦肩而過,可能閃耀出火光,那個火光可能很巨大,可以照亮彼此的生命,《生之曼陀羅》就是在講這樣的故事。


Q:這次Art For The Masses的主題為「我‧我們」,請再細談這個主題和《生之曼陀羅》的關連性。
A:我們的創作,是「我」,也是「我們」一起完成的,而我在創作的時候,最常碰到第二個我就是吳興國。我們兩個都是彼此的第二個我,我們很像一個大肉球,只不過是被撕扯變成一半,像希臘悲劇一樣,分不清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不過有時候我更覺得他就像是我的小孩,他是不是我生出來的呢?

Q:所以兩個人之間可以不用言語溝通就彼此瞭解?
A:應該是說我猜他猜得準,他猜我猜不準,哈。
比方說當我看到他在偷笑,我就知道他背著我偷做了什麼壞事;你們看他的樣子,會覺得他很嚴肅,但其實他是很怕陌生人的,而且他非常調皮,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記得我女兒還小的時候,他們兩個會在餐廳裡面打來打去,我覺得好可怕,這麼老的人怎麼還在那邊跑來跑去。不過他也很容易生氣,我覺得他就像是幼稚園大班的小孩,而且是全班最難帶的那個,他可能會爬到樹上,又會躲在牆角不跟你講話,耍自閉。
Q:耍自閉的時候,是期待大家瞭解他嗎?
A:他不會,他根本不甩(笑)。
Q:彼此在生活或是創作上相互扮演的角色?
A:我覺得他是一塊石頭,而他覺得我像水,水可以移動石頭到原本不願意去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也覺得我像火,所以我就是水和火的綜合體。有時候,他也可以說是一棵樹,紮好根後,哪裡都不願意去,情願孤芳自賞,但是我會給他水,給他陽光,讓他再多開點花。
在工作上,我則是個工作狂,吳興國都叫我鐵娘子,但是因為有我,他才有安全感。聽說如果表演之前我還沒有出現,吳興國就會在那邊走來走去,只要我一出現,他就會安心下來。有趣的是,我女兒說我和吳興國不是愛人,是兄弟。
Q:這和我們的既定印象不太一樣。
A:對,其實我們就像太陽和月亮一樣,都有著陰陽兩面不停地在交換,無論是溫度或明暗度,所以在《生之曼陀羅》中有一些雙頭獸的造形,一個身體兩個腦袋,這就是我們相處的表現。





Q:這次Art For The Masses也邀請向京和瞿廣慈一同參與,可以跟我們分享對於他們作品的看法嗎?
A:我覺得向京的心思很細膩,她的作品好像一直保持在15、16歲少女的狀態,皮膚彈指可破,要被小心地保護著,放在一個永恆的花園裡面,不受污濁世界的沾染。我覺得女性很適合收藏她的作品,因為女人心中總保有對這世界嚮往的一處,而向京則是把那一刻留在她的作品裡。
瞿廣慈則是用作品來嘲笑這個世界的體制,諷刺人的權力就像打腫臉充胖子,雖然胸懷大志,長了翅膀,可卻是飛不起來。這隻鳥所佔領的樹,也是一顆假樹,像個謊言,就像莎士比亞說的,假樹怎麼會結出真的果子呢。所以他透過作品影射社會、政治的樣貌都是虛假的。



Q:「身體」是雙方創作的一個共通性,可否跟我們分享在這件作品中,雕塑和舞蹈表現身體形式的差異?
A:在向京的作品中,我看到某種優雅的姿態,脖子很長,身體很纖細,像精靈一樣。而看我們的作品,我覺得我是女巫,而向京是精靈,不過,精靈與女巫也是同一件事,輕靈是種力量,毀滅也是,這是二元的,是土地和天空的力量,可以互換。
Q:怎麼看待這次「跨領域」的合作方式?
A:其實跨領域對我們並不陌生,只是以前是由我們為本體,邀請別的藝術家,比方說葉錦添、張大春、徐克。這次比較是「對話性」的,很像是彼此相連,又有交錯,但是又分道揚鑣,只是有一個共同的核心精神,來講述「我」跟「我們」之間的故事,從肢體或是從美術上,有點對照的感覺。
Q:談談這次《生之曼陀羅》的呈現形態,從現場的舞蹈表演轉變成手動影像的表現,您怎麼看待作品呈現方式的改變?
A:我覺得這樣的處理方式很有趣,把我們縮得很小,縮在一個古老的鏡頭裡面,還蠻神秘的。因為《生之曼陀羅》其實是個慾望的世界,框在裡頭,好像是人生愛情的顯微鏡,挺有意思的。
而用手動操作的方式,讓觀者參與表演,觀看的當下就像是在表演觀者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這樣的展出方式,就像創造了一個機會說觀賞者的故事,《生之曼陀羅》就不只是我和吳興國的故事。



Q:這次重新演出《生之曼陀羅》,和之前的演出有什麼樣的改變?
A:其實我和吳興國已經快10年沒有一起跳舞了。這次我們一次排練都沒有,就這樣子去拍了,一次就成功了,我自己也感到很驚訝。吳興國說我除了重了一點以外,沒有什麼改變,不過既然他還抬得動我,所以我也沒那麼重嘛(笑)。
 1988年我們跳完《生之曼陀羅》後,我女兒就出生了,而這次展覽的記者會,也請我女兒跳一支舞(右圖),為展覽開場,所以若說這隻舞和過去有什麼不一樣?我想,應該是多了「傳承」這個意義。
1988年我們跳完《生之曼陀羅》後,我女兒就出生了,而這次展覽的記者會,也請我女兒跳一支舞(右圖),為展覽開場,所以若說這隻舞和過去有什麼不一樣?我想,應該是多了「傳承」這個意義。Q:如果有來生,兩位還想再當夫妻嗎?
A:吳興國曾經對我說他來生想變成一棵樹,我聽到以後,就笑著回答他:「那我要變成樹上面的那隻猴子,你想要安靜,我就在你身上盪來盪去,讓你不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