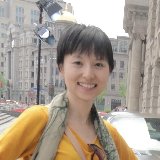就算台,也可以台得優雅──盧昉與布魯哲爾的訪台之旅
在「大鼻子的異想世界」中,呈現了藝術時序的古今錯置,「突兀」成了共同的寫照,也映照出盧昉當時處在生命的叉路,第一時間不知該如何反應的無奈與感懷。

《大鼻子與聖母》
而這次「出古入今Ⅱ:玩轉古畫」的展覽,大鼻子不再回到過去,而是邀請文藝復興時期畫家布魯哲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來到現代台灣,和盧昉完成一次跨界的合作。同樣也是穿越古今的中西對話,只是話語不再突兀,反而共譜優雅的和諧詩意,並流洩出些許思古懷舊的情愫。
盧昉說,他的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歲月都在海外漂泊。面對台灣,他一開始帶著懷疑的審視眼光。後來,住在國外久了,對於台灣的思念,可以來自一份士林夜市豪大雞排的召喚;撫慰味覺,得由一杯折合新台幣 250 元的珍珠奶茶才能完成。原來,味覺也有鄉愁。或許身處異文化的疏離與陌生,才能讓熟悉的知覺更顯深刻,才能揭開過往糾結關乎自我、認同與生命的層層迷團,而走向面對自身的坦途。
從 「大鼻子的異想世界」到「玩轉古畫」,就像是盧昉對於自己生命認同的探尋,而這段歷程,並非一般寒徹骨的轟轟烈烈,而是維持慣有的優雅,融合衝突,最後交疊出一首首中西吟唱的和諧曲目。於是,他笑納台灣的混亂、嘈雜,調適成他自己的一套生活美學,就算「台」,也可以台得優雅,而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為何發生?且讓我們一起跟著盧昉出古入今,玩轉古畫,一探究竟。



A:在「大鼻子的異想世界」中,我希望讓人家進到這個展場後有一個錯覺,就是這些作品看似是古代大師畫的,而不是我畫的,所以在作品年代我會標上 15 世紀、16 世紀。
在古代,「複製」和「挪用」古畫很普遍,我就想說是否可以做出屬於我的版本,是我穿越時空進入那幅畫當時的場景,很像我們一群人在外面旅遊,腳架架好要一起合照時,剛好有個路人甲從前面走過去,結果那位路人甲就入鏡了,有一點惡搞的成分。所以在凡艾克(Jan van Eyck)那幅《阿諾菲尼與他的新娘》(下左圖),我就把新郎趕出去,換成是我,就成了《大鼻子與他搶來的新娘》(下右圖)。


這次個展「玩轉古畫」不同處在於我把古典帶入當代,是由我和布魯哲爾共同完成,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跨界合作,跨了 500 年,跨了 1 萬公里,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一個實驗。
Q:為什麼這次是以布魯哲爾做為合作對象?
A: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北方文藝復興畫派的風格,包括凡艾克、維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布魯哲爾,他們保有尼德蘭早期纖細畫的傳統,非常強調細節。
布魯哲爾是我小學就認識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很像童話繪本,像安徒生童話的插畫感覺,沒有那麼嚴肅,有點童趣,會選擇他也是考慮到,我的創作與他的作品兩者間連結的可能。
Q:可能性是什麼?
A:像凡艾克和維登的作品是以人物為主,人物非常大,所以能夠發揮的部分比較少。布魯哲爾的作品是場景比較大,很像用超廣角的鏡頭在看一個都市,我有置換物件的可能性,可以發揮的空間相對也比較大。
像他的《興建巴別塔》(下圖上排),就是《聖經》創世紀中有說過的一件事情,我覺得這幅圖很有趣,就把這件作品和景美的城市景觀結合在一起,變成了《台北大違建》(下圖下排)這件作品。

布魯哲爾作品《興建巴別塔》。


《台北大違建》(上上圖為局部,上圖為全景)一作,是盧昉較少嘗試的大畫幅作品,盧昉將台北的俯瞰圖結合布魯哲爾的《興建巴別塔》,像是為台北建造一座大地標,也將台北特有的樣貌記錄在畫作之中。
Q:從作品來看,《辦桌圖》是援用布魯哲爾的《農民婚禮》,為什麼會將這件作品和台灣的「辦桌文化」結合在一起?
A:在畫這張《辦桌圖》(下圖上排)時,我也正在辦自己的婚事,那時候每個週末都要去看飯店,去選菜。對我來說,《農民婚禮》(下圖下排)這件作品就是 16 世紀的辦桌,是當時勞動階層的婚禮形式。
我覺得布魯哲爾的作品有種跨時間的台味,一種俗味,那時看到這件作品,我就想到如果換成辦桌,應該會很有趣。所以我就開始觀察辦桌,常跑到中南部去看,跑到人家的婚禮會場,說不好意思借我拍個照(笑),從中觀察辦桌文化的人與物。

盧昉此次展出作品《辦桌圖》

布魯哲爾作品《農民婚禮》
Q:之前對於台灣辦桌文化的想法是什麼?
A:之前完全不熟悉,甚至是嫌惡。我是在國外長大的,小學 4 年級才回到台灣,而且我家是外省家庭,住在台北,所以從小和台灣在地文化是有距離的。
可是曾幾何時,我在歐洲住久了,會想念自己的家鄉。在國外才會去思考,「什麼是台灣?」、「什麼是台灣人?」,所以當我留學後回來,面對過去曾經嫌惡過的鐵皮屋、招牌、雜亂的車陣,突然覺得可以接受,這就是家鄉的一個部分,也開始產生興趣。於是就把這些文化或是都市景觀,帶到我的作品之中。
Q:所以創作的過程也是尋找台灣認同的一個過程?
A:是。某種程度上,我的作品呈現我自己整個生命的狀態。因為我爸爸是駐外人員,小時候都在漂泊,常常一兩年就要搬一次家,我自己又是在國外長大,這些種種會讓我思考自己是屬於哪裡?歸屬何處?到底什麼是「家」?


在「大鼻子的異想世界」系列中,大鼻子(盧昉分身)穿梭到古畫中,像個路人甲誤入鏡頭一樣,帶有突兀之感,而這剛好與剛回台的盧昉當時的心境相合。左圖為《大鼻子的藝術》,右圖為《大鼻子歐使節》。
Q:對於台灣從「嫌惡」到「接受」的這個心境轉變,如何反映在你的創作上?
A:「大鼻子的異想世界」的作品都有一種「突兀」,作品很不協調,這種「不協調感」是我在創作時,真實發生的事情。記得我剛回台灣的第一個星期,是沒有辦法過馬路的,在國外過馬路,車子會停下來讓你,回來後發現這個地方的車子,怎麼會「咻」地從你前面穿過去(笑)。
但慢慢地一年過去、兩年過去,可能對這狀況還是不滿意,不過可以接受,OK 這是我的家,這是我的土地,我屬於這裡。
Q:另外,《古今人車爭道》(下圖)這幅畫作則是結合布魯格爾的《孩子們的遊戲》和台北的都市面貌,這件作品在什麼情境下創作出來?
A:我在做這件作品的時候,剛好生活環境面臨到都市更新的情況。你看作品的左上方,其實已經是都更過後的狀態,這幾年因為工作室在城中藝術特區,長時間觀察萬華區和中正區,感覺這些地方變化很大。
透過這件作品,我想要表達城市新舊之間的這種落差。有些作品也是給台北的一個紀念,是我和布魯哲爾一起合建的台北紀念碑,是對於過去一種淡淡的思念。我是一個還蠻懷舊的人,我把這個情感表現出來,然後再開點小玩笑。

此次展出作品《古今人車爭道》
Q:有幾張大鼻子肖像畫也是這次的展覽作品,肖像畫對你有什麼樣的意義?
A:這些肖像畫其實就是記錄自己。畫一幅畫,會有一段觀察時間,也呈現當時整個心理狀態,因此每年的自畫像會有不同,比方說我今年用紫色、把自己畫成胖子,明年搞不好會畫成瘦子。這些跟自己當時創作的喜好、生活遭遇有一定的關係,因此我認為這樣的紀錄是更全面的。透過一張自畫像,可以知道自己那時候遇到了什麼事情,所以用色特別重等等。


左圖:《戴紅帽的大鼻子》。右圖:《瑪格麗特大鼻子》。
Q:從創作風格看,你似乎是以一種「西方古代」的藝術眼光,來詮釋「台灣當代生活」,你個人怎麼看待這樣既跨「中西」又跨「古今」的結合?
A:這其實是我生命的一段經歷。我很喜歡古典的藝術,愛聽古典音樂,但我也是一位 30 多歲的台灣年輕人,我也喜歡 3C 產品,喜歡玩電動,這些同時並存在我的生命中。
我有超過 10 年的時間都在國外,我的內在是交錯著東西方文化。我覺得畫出這一張張模仿的古畫,就像在演戲,像是演著另外一個人,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自己就不見,有時候也是透過一個劇本,在講自己的生命故事。

Q:你的創作自述中曾提到:「作為一個台灣年輕當代藝術工作者,身上乘載著萬斤重的古歐洲沈重包袱,持續迷航中...」,現在還在迷航中嗎?還是已經有看到一座燈塔的光?
A:迷航是一個找尋的過程,我也不知道 10 年之後我會做什麼樣的創作,創作就是一邊前進,一邊找尋的;但是迷航不是漫無目的,很像是在一片大海中,尋找要前進的方向。我的創作就是跟著我的生命狀態,記錄我的人生,只是,生命也不是可以完全確定的。
Q:所以才要繼續航行下去?
A:對,會繼續航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