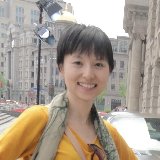如果野獸甦醒之後,世界會如何?──「獸醒」,蔡宜儒的人文關懷宣言
一切就從野獸甦醒之後開始說起……。
猴子組成機關槍部隊,攻克人類;鳥兒不再嬌柔可愛,張牙舞爪地伸向人類世界;野獸開始反撲人類,一場人獸世界大戰儼然開打。這是蔡宜儒新展「獸醒」中的想像世界,蔡宜儒透過大膽直率的筆觸、強烈的色彩,勾勒出一場人與獸的戰場,甘地曾說:「一個國家的道德進步及偉大程度,可用他們對待動物的方式衡量。」而蔡宜儒則透過畫筆,展現對人類行為的反思,傳達出對於動物的關懷。
猴子組成機關槍部隊,攻克人類;鳥兒不再嬌柔可愛,張牙舞爪地伸向人類世界;野獸開始反撲人類,一場人獸世界大戰儼然開打。這是蔡宜儒新展「獸醒」中的想像世界,蔡宜儒透過大膽直率的筆觸、強烈的色彩,勾勒出一場人與獸的戰場,甘地曾說:「一個國家的道德進步及偉大程度,可用他們對待動物的方式衡量。」而蔡宜儒則透過畫筆,展現對人類行為的反思,傳達出對於動物的關懷。
過去以植物、盆栽為繪畫主題的蔡宜儒,在 MOT/ARTS 的最新個展「獸醒」,改以動物為探討對象。第一次看到蔡宜儒的「獸醒」時,說真格的,還來不及在古拙、童趣的線條中體會動物造型的趣味,就先感受到一股濃濃的火藥味。溫馴的鳥兒有了尖牙利嘴,恐龍開始攻擊領空,輕易將飛機攔截到手,人類世界出現紅色危機,如果野獸就此甦醒……。
毫無疑問,蔡宜儒的「獸醒」給了觀者一個震撼性的開場,直觀性的線條刻畫與大膽澎湃的色彩使用,或塗、或抹、或刮的肌理,表現一種接近神經質的官能體驗,這是蔡宜儒全屬赤誠之心的告白。原本可與自然共享榮枯的動物們,卻因人類的私欲,成為寵物或是利益下的犧牲品,萬物生態的平衡也為之傾斜。
或許,「獸醒」是蔡宜儒內心最真摯的呼喊,只是,他試圖喚醒的不是原始的野獸力量,而是長存於人類內心的愛與關懷。那麼,在獸醒之後,蔡宜儒對於人獸並存的世界有什麼想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還是迎向一個人獸並存的美麗新世界?就讓我們一起跟隨蔡宜儒進入野獸甦醒之後的想像世界,一探究竟。

Q:從創作主題來看,過去「栽界」、「慾盆栽」等展覽是以植物為表現對象,而這次「獸醒」一展改以動物為主題,原因是什麼呢?
A:從植物轉向動物,看起來好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對象,其實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演變過程,有著內在共通性。我經常思考人跟動植物的互動關係,比方說「盆景」,一開始並沒有這種東西,是文人雅士遊山玩水時,帶點種子回家種,而成為那個時代的微型風景,融入人類生活。
動物本來跟人也是有距離的,有自己的生存世界,卻因為人的私欲,不管是善意還是利益性的,改變了動物的原始狀態和生活方式。所以這次的展覽,我試圖去傳達我眼中人與動物的關係。
這次的議題其實是沉重的,不過,我選擇用一種比較童趣、帶有赤子之心的方式去表現,用半抽象的語彙,讓觀眾思考為什麼我選擇這個主題,用什麼樣的內容去回應這部分,畫作其實帶有反思成分。

《獸醒》這張作品,左右兩邊分別是兩隻野獸(恐龍與獅子),張嘴咬著中間的人。恐龍是遠古時代最強大的野獸,獅子是現代的萬獸之王,這樣的選擇有時空的對照,也有時間性的暗示,不同時空的野獸都在反撲人類,是野獸對生存現況不滿的表達。(Photo credit:MOT/TIMES)
Q:談談《嗜》與《咬飛機的恐龍》這些作品,為什麼選擇恐龍、貓這些動物?
A:《嗜》是一個人在咬著一隻貓,造型、色彩看起來討喜,但是內容有點殘忍、血腥。這也是我用直觀的方式來表現人對動物的傷害。事實上,我們不會直接就把貓拿來咬啦(笑)。
《咬飛機的恐龍》(下圖)也是表現一種反撲。但是恐龍的時代不會有飛機的出現,飛機出現的時候,恐龍也已經滅絕了。這是用時空的錯置來增加矛盾衝突的戲劇性,飛機代表人類文明的高度,恐龍代表和文明對立的衝突,有點類似酷斯拉攻擊人類的場景。

咬飛機的恐龍 油彩 畫布 130x194cm 2012

猴子開機關槍 油彩 畫布 130x194cm 2012
Q:覺得自己是畫中哪一隻動物的投射?
A:恐龍吧~那種張牙舞爪、有攻擊性的,比較接近潛意識的我。
但是我跟人相處時,就蠻正常的,可以理性溝通。只是創作時,就會出現反差的性格,處在創作狀態時,我不習慣有人在旁邊看,會變得有點神經兮兮的(笑)。
Q:這次的創作技法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談一下這個部分嗎?
A:一方面是對自我突破的期許,我也可以用以前的山水技法來呈現,但是總覺得還有很多技巧可以去嘗試,所以有了調整。
另外,以前在畫盆景(下圖)的時候,是以書法線條、潑墨、大寫意的方式和西方抽象表現主義做融合。這次的作品,我拿掉書法性的線條,用古拙式的線條、塗鴨的方式來表現。我也在顏料未乾的時候,用刮的方式來表現質感,讓撕裂的表情可以更逼真、更神經質,精神性的投射更能呼應這次的主題。

盆景舞松風 綜合媒材 畫布 82x110cm 2010
Q:從「慾盆栽」、「土養──沈思者」、再到「獸醒」,儘管展出主題不同,卻都可以看見作品中蘊藏不同類型的力量,包括慾望流動的張力、大地的衝擊力、動物原始暴力等?
A:對,這些力量其實就是創作的骨幹,也是我的本質,我就是去正視它,接受它,然後傳達它。這兩三年,為了求自我突破,我也會嘗試用比較理性、冷靜的方式來創作,理性的美感可以變成一張畫,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不屬於我,看久了反而覺得陌生。
像「慾盆栽」的水墨潑灑,有點類似潛意識書寫,或者是「獸醒」的肌理表現,會看到我的精神投射在裡面,很像照鏡子的感覺。作品是要很誠實的,不然力量會被扭曲,不管是什麼類型的作品,一定會有個質地貫穿其中。

盒裝2℃沉思者 壓克力顏料 油彩 畫布 146x227cm 2011

沉思者--孩童與大地 壓克力顏料 油彩 畫布 150x170cm 2011
Q:就你的創作方法來看,個人的感知與生活的體悟如何化做自己的創作靈感?
A: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在生活中體驗與累積靈感。這幾年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體驗,就是前年去日本常滑市駐村。駐村時我選擇住在日本人家裡,而當時提供住宿的爺爺給了我很多人生上的啟發,那是最初沒有預料到的體驗。
Q:老爺爺也是藝術家嗎?
A:不是,他是藝文的愛好者,他喜歡茶道、插花、標本等。他曾中風過,現在一個人住,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必須自己來。我跟他生活兩個星期,不算長,他總是用著一種不慍不火,卻很有誠意的方式招待我,我可以感受到他用最真誠的態度去對待當下的每一件事情,不求預期性的回報,而這點影響我很多。
這件事或許聽起來和創作無關,但是藝術和生活不能切割。這是一個面對自我的生命態度,給我很大的啟發與感動,也漸漸影響我去感受當下的每一個狀態,讓我更有動力去落實自己對於藝術的理想。
Q:這個生活經驗對創作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或改變?
A:我以前在畫「盆栽」這個主題,對於觀眾來說,比現在這個「獸醒」展要有人文味。因為「盆栽」就帶有歷史性的投射,代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所以我只要選這個主題,就有人文的意涵。但是從內容面來說,其實有點虛,因為這只是一種選擇,並沒有投射我個人的人文關懷。
在日本生活過後,我覺得自己比較可以具體的表現內心情感,尤其到了「獸醒」這個階段,主題對象才更具體的表現出來,不只是對於動物,也可以說是對人的一種關懷。

作品《驚懼的動物》,蔡宜儒透過「獸醒」系列,表達對於動物的關懷。
Q:有沒有想過「獸醒」之後,人類和動物之間的關係?
A:我覺得充滿無限可能。我看過一部電影,裡面是動物在走秀,動作和我們現在時尚模特兒一樣,只是身上穿的是人類的器官,而且設計得很可愛、很華麗。
鏡頭一轉,帶到後台,是很多人無辜地被關在籠子裡,人類和動物的世界是整個反過來的。其實野獸的獸性力量遠大於人類,可是因為人類太聰明了,所以是我們統治著這個世界。我想,人類的力量還是會繼續變大,只是真的要多點反省,這不只是人和動物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毫無疑問,蔡宜儒的「獸醒」給了觀者一個震撼性的開場,直觀性的線條刻畫與大膽澎湃的色彩使用,或塗、或抹、或刮的肌理,表現一種接近神經質的官能體驗,這是蔡宜儒全屬赤誠之心的告白。原本可與自然共享榮枯的動物們,卻因人類的私欲,成為寵物或是利益下的犧牲品,萬物生態的平衡也為之傾斜。
或許,「獸醒」是蔡宜儒內心最真摯的呼喊,只是,他試圖喚醒的不是原始的野獸力量,而是長存於人類內心的愛與關懷。那麼,在獸醒之後,蔡宜儒對於人獸並存的世界有什麼想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還是迎向一個人獸並存的美麗新世界?就讓我們一起跟隨蔡宜儒進入野獸甦醒之後的想像世界,一探究竟。

Q:從創作主題來看,過去「栽界」、「慾盆栽」等展覽是以植物為表現對象,而這次「獸醒」一展改以動物為主題,原因是什麼呢?
A:從植物轉向動物,看起來好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對象,其實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演變過程,有著內在共通性。我經常思考人跟動植物的互動關係,比方說「盆景」,一開始並沒有這種東西,是文人雅士遊山玩水時,帶點種子回家種,而成為那個時代的微型風景,融入人類生活。
動物本來跟人也是有距離的,有自己的生存世界,卻因為人的私欲,不管是善意還是利益性的,改變了動物的原始狀態和生活方式。所以這次的展覽,我試圖去傳達我眼中人與動物的關係。
這次的議題其實是沉重的,不過,我選擇用一種比較童趣、帶有赤子之心的方式去表現,用半抽象的語彙,讓觀眾思考為什麼我選擇這個主題,用什麼樣的內容去回應這部分,畫作其實帶有反思成分。

《獸醒》這張作品,左右兩邊分別是兩隻野獸(恐龍與獅子),張嘴咬著中間的人。恐龍是遠古時代最強大的野獸,獅子是現代的萬獸之王,這樣的選擇有時空的對照,也有時間性的暗示,不同時空的野獸都在反撲人類,是野獸對生存現況不滿的表達。(Photo credit:MOT/TIMES)
Q:談談《嗜》與《咬飛機的恐龍》這些作品,為什麼選擇恐龍、貓這些動物?
A:《嗜》是一個人在咬著一隻貓,造型、色彩看起來討喜,但是內容有點殘忍、血腥。這也是我用直觀的方式來表現人對動物的傷害。事實上,我們不會直接就把貓拿來咬啦(笑)。
《咬飛機的恐龍》(下圖)也是表現一種反撲。但是恐龍的時代不會有飛機的出現,飛機出現的時候,恐龍也已經滅絕了。這是用時空的錯置來增加矛盾衝突的戲劇性,飛機代表人類文明的高度,恐龍代表和文明對立的衝突,有點類似酷斯拉攻擊人類的場景。

咬飛機的恐龍 油彩 畫布 130x194cm 2012

猴子開機關槍 油彩 畫布 130x194cm 2012
Q:覺得自己是畫中哪一隻動物的投射?
A:恐龍吧~那種張牙舞爪、有攻擊性的,比較接近潛意識的我。
但是我跟人相處時,就蠻正常的,可以理性溝通。只是創作時,就會出現反差的性格,處在創作狀態時,我不習慣有人在旁邊看,會變得有點神經兮兮的(笑)。
Q:這次的創作技法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談一下這個部分嗎?
A:一方面是對自我突破的期許,我也可以用以前的山水技法來呈現,但是總覺得還有很多技巧可以去嘗試,所以有了調整。
另外,以前在畫盆景(下圖)的時候,是以書法線條、潑墨、大寫意的方式和西方抽象表現主義做融合。這次的作品,我拿掉書法性的線條,用古拙式的線條、塗鴨的方式來表現。我也在顏料未乾的時候,用刮的方式來表現質感,讓撕裂的表情可以更逼真、更神經質,精神性的投射更能呼應這次的主題。

盆景舞松風 綜合媒材 畫布 82x110cm 2010
Q:從「慾盆栽」、「土養──沈思者」、再到「獸醒」,儘管展出主題不同,卻都可以看見作品中蘊藏不同類型的力量,包括慾望流動的張力、大地的衝擊力、動物原始暴力等?
A:對,這些力量其實就是創作的骨幹,也是我的本質,我就是去正視它,接受它,然後傳達它。這兩三年,為了求自我突破,我也會嘗試用比較理性、冷靜的方式來創作,理性的美感可以變成一張畫,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不屬於我,看久了反而覺得陌生。
像「慾盆栽」的水墨潑灑,有點類似潛意識書寫,或者是「獸醒」的肌理表現,會看到我的精神投射在裡面,很像照鏡子的感覺。作品是要很誠實的,不然力量會被扭曲,不管是什麼類型的作品,一定會有個質地貫穿其中。

盒裝2℃沉思者 壓克力顏料 油彩 畫布 146x227cm 2011

沉思者--孩童與大地 壓克力顏料 油彩 畫布 150x170cm 2011
Q:就你的創作方法來看,個人的感知與生活的體悟如何化做自己的創作靈感?
A: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在生活中體驗與累積靈感。這幾年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體驗,就是前年去日本常滑市駐村。駐村時我選擇住在日本人家裡,而當時提供住宿的爺爺給了我很多人生上的啟發,那是最初沒有預料到的體驗。
Q:老爺爺也是藝術家嗎?
A:不是,他是藝文的愛好者,他喜歡茶道、插花、標本等。他曾中風過,現在一個人住,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必須自己來。我跟他生活兩個星期,不算長,他總是用著一種不慍不火,卻很有誠意的方式招待我,我可以感受到他用最真誠的態度去對待當下的每一件事情,不求預期性的回報,而這點影響我很多。
這件事或許聽起來和創作無關,但是藝術和生活不能切割。這是一個面對自我的生命態度,給我很大的啟發與感動,也漸漸影響我去感受當下的每一個狀態,讓我更有動力去落實自己對於藝術的理想。
Q:這個生活經驗對創作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或改變?
A:我以前在畫「盆栽」這個主題,對於觀眾來說,比現在這個「獸醒」展要有人文味。因為「盆栽」就帶有歷史性的投射,代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所以我只要選這個主題,就有人文的意涵。但是從內容面來說,其實有點虛,因為這只是一種選擇,並沒有投射我個人的人文關懷。
在日本生活過後,我覺得自己比較可以具體的表現內心情感,尤其到了「獸醒」這個階段,主題對象才更具體的表現出來,不只是對於動物,也可以說是對人的一種關懷。

作品《驚懼的動物》,蔡宜儒透過「獸醒」系列,表達對於動物的關懷。
Q:有沒有想過「獸醒」之後,人類和動物之間的關係?
A:我覺得充滿無限可能。我看過一部電影,裡面是動物在走秀,動作和我們現在時尚模特兒一樣,只是身上穿的是人類的器官,而且設計得很可愛、很華麗。
鏡頭一轉,帶到後台,是很多人無辜地被關在籠子裡,人類和動物的世界是整個反過來的。其實野獸的獸性力量遠大於人類,可是因為人類太聰明了,所以是我們統治著這個世界。我想,人類的力量還是會繼續變大,只是真的要多點反省,這不只是人和動物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