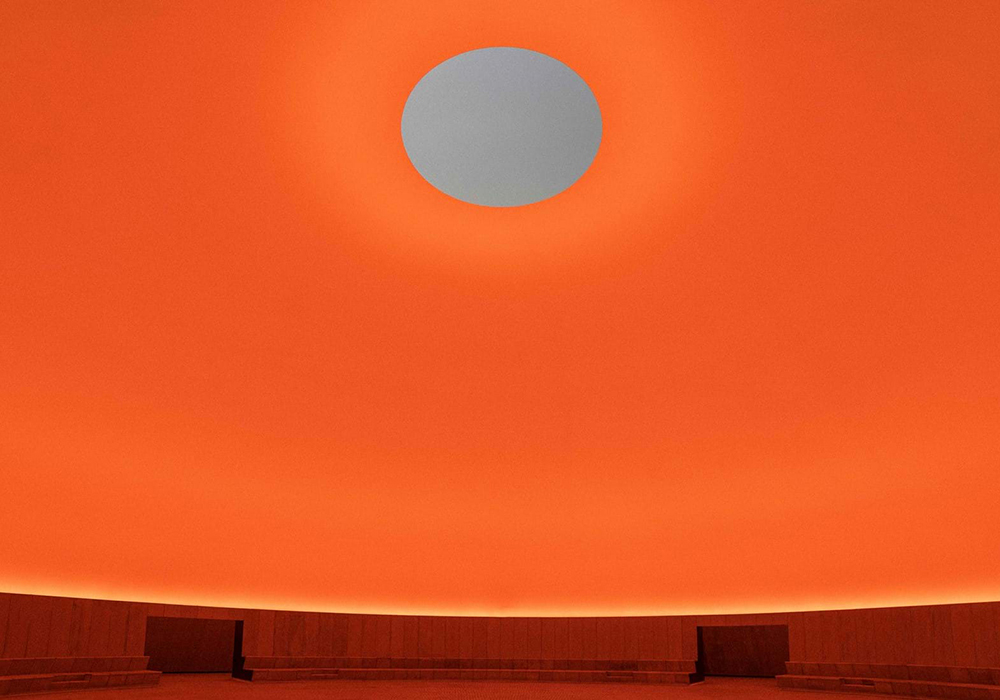落幕之後,還有什麼是持續的?——柏林雙年展現場直擊
人類存在多少年,政治議題、政治紛爭便一同相伴多少年,而高喊著「忘記恐懼」的柏林雙年展(Berlin Biennale),主張藝術該有其力量,將政治議題納入藝術展覽中,3個月過去了,展覽落幕了,而這樣一個勇敢但也許無法獲得解答的雙年展,到底是為參與的觀展者與社會投下一顆無法逃避的震撼彈,還是有其名卻無意義的煙霧彈?
第 7 屆柏林雙年展已在 7 月落幕,它體現了展覽所在地——柏林這座城市的無比反叛:開展前就以捷克藝術家馬丁‧賽特(Martin Zet)集中焚毀反移民理論書籍的集權激進手法引爆爭議、邀請占領團體(Occupy)在展期間進駐 KW 當代藝術中心、葉‧芭塔娜(Yael Bartana)號召三百萬猶太人重返波蘭,甚至還有恐怖份子參與的世界高峰論壇……,這些事件理當出現政治版的頭條,但裹上「藝術概念」及「展覽形式」的糖衣後,它們仍很難稱得上鮮艷好看,這究竟是一場顛覆邏輯、意義全無的煙霧彈,或是個將荒謬的現實搬上藝術的舞臺的認真表演?


KW 展場的一樓及地下室被席捲全球的占領團體占據,但很不同的是,此次他們是被邀請入室。
讓我們先回到柏林雙年展的背景,1998 年首屆柏林雙年展因應歐陸雙年展的熱潮而生,迄今其規模與知名度雖還無法與威尼斯雙年展或卡塞爾文件展等世界大展相比擬,卻已然成為與城市歷史發展最緊密連結的當代藝術雙年展代表。而世界上可能再也沒有比柏林更具有傳奇色彩的城市了,歷經了分裂與統一、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瓜分、納粹的種族屠殺……。這裡深深地刻劃著戰爭的傷痕和歷史民族的瘡疤,然而德國統一後的二十年來卻一直以優越的政經條件在一片歐債危機中穩站歐洲引領者地位;這裡更孕育了無數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並且現在柏林以低廉的房租及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許多國際藝術家定居創作,已搖身變成了藝術家的首選築夢之地。柏林同時有最沉重的歷史和最輕盈奔放的自由,於是再高的牆都能倒下,再不可能的理念都能被付諸行動。
本屆來自波蘭的策展人兼藝術家亞特‧祖米卓斯基(Artur Żmijewski)將展覽標題定為「忘記恐懼」(Forget Fear),十足帶有政治宣傳口號的熱度,姑且先不論煽動的程度和成果,這樣的企圖在很多層面上都一一彰顯了:首先是讓主客易位,展出的不是文化菁英,而是讓社會邊緣者甚至是被禁者,進駐雙年展挑戰藝術及藝術機構定位,反向地為亞特認定為「腐敗、軟弱、妥協」的藝術機構發聲。有趣的是,散場之後是否邊緣者仍是邊緣者,藝術機構便回復到主宰主流意識形態的藝術機構呢?策展人藉雙年展欲實現的「藝術發揮實際作用,並讓政治有空間實踐(perform)」,是否的確藉由展覽把政治的效能發揮了?抑或僅是在展期內供給這些政治性活動一個短暫的「表演」之處?


Khaled Jarrar 設計的巴勒斯坦簽證章,以及參與的各國民眾與蓋章後的護照合照。
忘記恐懼之前,需要喚醒傷痛的感覺、挖掘恐懼的根源,這屆柏林雙年展展出的內容盡是對於中東政治衝突、領土問題、種族屠殺及墨西哥毒品等議題的表述與回應,踏入展場好比進入百家爭鳴的熱鬧場面,每個人努力爭取著發言權,卻沒有一個主持者調節展覽的節奏與脈絡;但也因為展覽被賦予了極度的自由,有許多作品還算成功地藉由互動性加強了觀者對這些事件的感知。例如踏入 KW 展場的一樓後,映入眼簾的是佈滿牆面地板的塗鴉與海報,裝扮稍怪異的占領者聚集著讓觀者迷惘怯步,但還是有些占領者主動與觀者互動,或替外國觀眾翻譯海報上的德文口號;此外,展場二樓一區展示著巴勒斯坦藝術家 Khaled Jarrar 自行創造的巴勒斯坦簽證章,一個長桌上滿佈著藝術家在爭議領土區邀請民眾加入蓋章活動的照片(上圖),照片裡許多參與者大大的笑容裡,看不見一絲因為在護照上表態支持巴勒斯坦主權,可能讓自己陷入麻煩的擔憂恐懼,這樣的柔軟在充斥著激進的展覽中反而顯得特別強而有力。KW 展場的頂樓,繼波伊斯的七千棵橡樹、第 12 屆卡塞爾文件展之後,再度不厭其煩的延續著德國每逢大展必「種樹」的藝術傳統: Lukasz Surowiec 將奧許維次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 )的樹苗(Auschwitz-Birkenau )移來柏林,邀請民眾認領帶回栽種,讓當年被帶走的無數生命藉由樹苗的滋長獲得另一種延續。

Lukasz Surowiec 自奧許維次集中營移來的樹苗,展期內開放參觀民眾自由認領。
雖然整體來看,柏林雙年展陷入一種將政治活動徹底移植到藝術體制內引發的混亂僵局裡,還是能發現將兩者完美結合的動人之作:在伯利恆難民營入口處的巨大鑰匙是作為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信仰指標,讓人們相信只要留著一把老家的鑰匙,回家之日終是指日可待的。今日藉由展覽將它運來柏林展示,讓這裡的觀眾看見如此遙遠飄渺的信念以鋼鐵的形式堅定的存在著,這不正是將藝術的力量做最單純而徹底的一種實踐?畢竟藝術政治性的存在並無法讓極端的議題馬上獲得救贖,但若是打開一個討論空間,也許將能開啟一種更廣大、更有包容性的可能。


從巴勒斯坦難民營運來的鑰匙象徵巴勒斯坦人們的回歸希望,上頭畫滿支持者的留言及塗鴉。
眾聲喧嘩之後,這些聲響是否隨著展覽落幕嘎然而止?雖然在動亂地區這些紛亂仍轟隆隆的響著,而聽見了這些孤注一擲的呼喊後的柏林依舊是柏林,但它們至少在柏林這自由的世界舞台、當代藝術的重鎮,熱切的告訴了世人除了經濟成長、資源分配不均、老年化、移民、環境等議題之外,仍有這些棘手的、最邊緣的,卻一直讓歐洲和整個世界噤聲的事件存在著。即使本屆柏林雙年展徹底脫離了美學的範疇,也即使並沒留下太多對社會實質的幫助或改變,這些聲音終究被記錄了下來。而做為歐洲最重要的展覽之一,柏林雙年展將今年的鎂光燈完完全全地獻給這些題材,也的確提供了一個值得各地觀眾深思的空間,不管是對於藝術自身或是這個世界。


KW 展場的一樓及地下室被席捲全球的占領團體占據,但很不同的是,此次他們是被邀請入室。
讓我們先回到柏林雙年展的背景,1998 年首屆柏林雙年展因應歐陸雙年展的熱潮而生,迄今其規模與知名度雖還無法與威尼斯雙年展或卡塞爾文件展等世界大展相比擬,卻已然成為與城市歷史發展最緊密連結的當代藝術雙年展代表。而世界上可能再也沒有比柏林更具有傳奇色彩的城市了,歷經了分裂與統一、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瓜分、納粹的種族屠殺……。這裡深深地刻劃著戰爭的傷痕和歷史民族的瘡疤,然而德國統一後的二十年來卻一直以優越的政經條件在一片歐債危機中穩站歐洲引領者地位;這裡更孕育了無數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並且現在柏林以低廉的房租及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許多國際藝術家定居創作,已搖身變成了藝術家的首選築夢之地。柏林同時有最沉重的歷史和最輕盈奔放的自由,於是再高的牆都能倒下,再不可能的理念都能被付諸行動。
本屆來自波蘭的策展人兼藝術家亞特‧祖米卓斯基(Artur Żmijewski)將展覽標題定為「忘記恐懼」(Forget Fear),十足帶有政治宣傳口號的熱度,姑且先不論煽動的程度和成果,這樣的企圖在很多層面上都一一彰顯了:首先是讓主客易位,展出的不是文化菁英,而是讓社會邊緣者甚至是被禁者,進駐雙年展挑戰藝術及藝術機構定位,反向地為亞特認定為「腐敗、軟弱、妥協」的藝術機構發聲。有趣的是,散場之後是否邊緣者仍是邊緣者,藝術機構便回復到主宰主流意識形態的藝術機構呢?策展人藉雙年展欲實現的「藝術發揮實際作用,並讓政治有空間實踐(perform)」,是否的確藉由展覽把政治的效能發揮了?抑或僅是在展期內供給這些政治性活動一個短暫的「表演」之處?


Khaled Jarrar 設計的巴勒斯坦簽證章,以及參與的各國民眾與蓋章後的護照合照。
忘記恐懼之前,需要喚醒傷痛的感覺、挖掘恐懼的根源,這屆柏林雙年展展出的內容盡是對於中東政治衝突、領土問題、種族屠殺及墨西哥毒品等議題的表述與回應,踏入展場好比進入百家爭鳴的熱鬧場面,每個人努力爭取著發言權,卻沒有一個主持者調節展覽的節奏與脈絡;但也因為展覽被賦予了極度的自由,有許多作品還算成功地藉由互動性加強了觀者對這些事件的感知。例如踏入 KW 展場的一樓後,映入眼簾的是佈滿牆面地板的塗鴉與海報,裝扮稍怪異的占領者聚集著讓觀者迷惘怯步,但還是有些占領者主動與觀者互動,或替外國觀眾翻譯海報上的德文口號;此外,展場二樓一區展示著巴勒斯坦藝術家 Khaled Jarrar 自行創造的巴勒斯坦簽證章,一個長桌上滿佈著藝術家在爭議領土區邀請民眾加入蓋章活動的照片(上圖),照片裡許多參與者大大的笑容裡,看不見一絲因為在護照上表態支持巴勒斯坦主權,可能讓自己陷入麻煩的擔憂恐懼,這樣的柔軟在充斥著激進的展覽中反而顯得特別強而有力。KW 展場的頂樓,繼波伊斯的七千棵橡樹、第 12 屆卡塞爾文件展之後,再度不厭其煩的延續著德國每逢大展必「種樹」的藝術傳統: Lukasz Surowiec 將奧許維次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 )的樹苗(Auschwitz-Birkenau )移來柏林,邀請民眾認領帶回栽種,讓當年被帶走的無數生命藉由樹苗的滋長獲得另一種延續。

Lukasz Surowiec 自奧許維次集中營移來的樹苗,展期內開放參觀民眾自由認領。
雖然整體來看,柏林雙年展陷入一種將政治活動徹底移植到藝術體制內引發的混亂僵局裡,還是能發現將兩者完美結合的動人之作:在伯利恆難民營入口處的巨大鑰匙是作為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信仰指標,讓人們相信只要留著一把老家的鑰匙,回家之日終是指日可待的。今日藉由展覽將它運來柏林展示,讓這裡的觀眾看見如此遙遠飄渺的信念以鋼鐵的形式堅定的存在著,這不正是將藝術的力量做最單純而徹底的一種實踐?畢竟藝術政治性的存在並無法讓極端的議題馬上獲得救贖,但若是打開一個討論空間,也許將能開啟一種更廣大、更有包容性的可能。


從巴勒斯坦難民營運來的鑰匙象徵巴勒斯坦人們的回歸希望,上頭畫滿支持者的留言及塗鴉。
眾聲喧嘩之後,這些聲響是否隨著展覽落幕嘎然而止?雖然在動亂地區這些紛亂仍轟隆隆的響著,而聽見了這些孤注一擲的呼喊後的柏林依舊是柏林,但它們至少在柏林這自由的世界舞台、當代藝術的重鎮,熱切的告訴了世人除了經濟成長、資源分配不均、老年化、移民、環境等議題之外,仍有這些棘手的、最邊緣的,卻一直讓歐洲和整個世界噤聲的事件存在著。即使本屆柏林雙年展徹底脫離了美學的範疇,也即使並沒留下太多對社會實質的幫助或改變,這些聲音終究被記錄了下來。而做為歐洲最重要的展覽之一,柏林雙年展將今年的鎂光燈完完全全地獻給這些題材,也的確提供了一個值得各地觀眾深思的空間,不管是對於藝術自身或是這個世界。